周萍萍 | 高田时雄与古汉语史研究
作者:周萍萍来源:《汉学研究》(总第三十集 2020年春夏卷)2021年8月时间:2022-05-11字号:【大】【中】【小】【打印】
摘 要:日本著名敦煌学家高田时雄是在战后日本敦煌学研究鼎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他以主攻的语言史研究为中心,一直耕耘于敦煌文献与汉语史的关联研究领域,别具一格,高识远见。高田教授运用语言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汉语音韵学、汉藏对音、河西方言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讨,取得了很多优秀研究成果,丰富了汉语史研究。同时,他还立足于国际视野,注重国家间的学术交流,本着传承敦煌文明的初衷,致力于国际敦煌学的发展和未来。
关键词:高田时雄 敦煌学家 古汉语史 研究
高田时雄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敦煌学家,是在战后日本敦煌学研究鼎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敦煌写本的语言史,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有《敦煌资料的中国语研究——九、十世纪的河西方言》(『敦煌資料によるの中国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1988)、《敦煌·民族·语言》(2005)、《汉字文化三千年(『漢字文化三千年』,2009)、《中国语史的资料和方法》(『中国語史の資料と方法』,1994)、《明清时代的音韵学》(『明清時代の音韻学』,2001)等论著和编著,以及《回鹘字音考》(「ウイグル字音考」,1985)、《于阗文书中的汉语词汇》(「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1988)、《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语言和敦煌写本的性格》(「慧超『往五天竺國傳』の言語と敦煌写本の性格」,1992)等著名论文。高田教授将古汉语研究与敦煌学相结合,发挥其卓越的语学才能,分析了中国多个时代及地区记录下的各种写本和刊本资料,论证严密,观点精辟,从汉藏对音资料、河西方言的语言史和敦煌古逸音韵文献3个方面,给我们勾勒出一段以人文社会的具体生活为背景的汉语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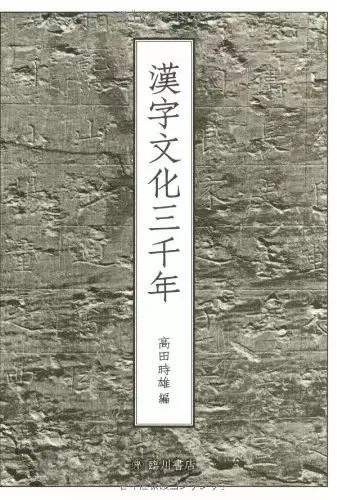
『漢字文化三千年』书影
一、敦煌汉藏对音资料的研究
高田教授于1968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6年赴法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就任京都大学教养学部副教授,1997年晋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直至2014年退休。京都大学的敦煌学研究历史悠久,也是日本敦煌学的发源地,内藤湖南(1866—1934)、狩野直喜(1868—1947)、羽田亨(1882—1955)和藤枝晃(1911—1998)等著名敦煌学家皆出自敦煌学京都学派。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高田教授立足于东亚敦煌学传统,以极高的水平融合欧洲东方学的研究视角,面对敦煌写本广杂的内容和多语种的特点,为敦煌写本及汉语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和新的框架,催生了广度与深度兼备的研究新领域。
针对敦煌写本与汉语史研究的关系,高田教授撰写了《敦煌遗书与汉语史研究》一文,总结了前人学者利用敦煌出土的古逸文献在汉语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以古逸文献为主的汉语史材料,如《切韵》《唐韵》《玉篇》,以及佛典音义、经籍旧音等敦煌出土的残片是早期敦煌遗书语言研究的主要对象,且已经取得颇丰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这些文献多反映的是中原文化,还应与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的语言史结合起来研究。
高田教授于1988年出版了《敦煌资料的中国语研究——九·十世纪的河西方言》一书,同年获得了第十六届金田一京助博士纪念奖。这本著作是高田教授在学位申请论文的基础上修订润色后出版的。书中仔细核实了藏于伦敦和巴黎的敦煌文献第一手资料,厘清了关于“汉藏对音资料”的过去所有研究成果,涵盖了《千字文》《金刚经》《阿弥陀经》《大乘中宗见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蕃会盟碑》等14种汉藏对音资料。他指出,汉藏对音资料的介绍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法国亨利·马伯乐(Henri Maspéro)的著作《唐代长安方言考》( Le dialecte de Tch'anga-ngan sous les Tang)引用了汉藏对音本《千字文》的部分内容。1923年,日本的羽田亨撰文《汉蕃对音千字文断简》(『漢蕃対音千字文の断簡』)介绍了附有藏文注音的《千字文》,并释读、转写了其中的汉藏对音,确定了其性质及与唐代西北方音的关系。之后,英国一些学者陆续介绍了音译为藏文的《金刚经》《阿弥陀经》《大乘中宗见解》等,而从30年代开始出现了以这些汉藏对音数据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较强的论著,如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言》等。
传统的汉语音韵史研究主要是把通过反切及注音整理划分出的用字分合情况与《切韵》系韵书的韵类相对照,分析其归并,同时使用外语中汉字借音资料作为推定音值的辅助材料。高田教授不仅使用了敦煌写本中汉文的注音资料,还特别提出资料可以通过语言的历史背景进行分层研究,这是他在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发现。他说道,藏文音译的汉文资料尚有许多收藏于英法两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7年,其概况才介绍给学术界。数据数量一举增加,相互比较成为可能,因此数据的层次才清楚了。
基于此,高田先生在其著作中将收集到的14种汉藏对音资料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长安音,亦称A类,是以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碑文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名等对音为标尺,分析出其音韵特征与唐代长安音较为接近;第二类为河西音,亦称B类,特征是全浊声母均有无声化现象。
罗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以汉藏对音的音韵学分析为主,而且参酌注音本《开蒙要训》、唐蕃会盟碑等的研究,长期在音韵学界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成书时间较早,采用的资料有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高田先生新增补了罗书中未能利用的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汉藏对音资料,指出罗书在利用资料时存在缺陷,未注意到资料间的性质差异和整体的层次,而且使用的对音资料均属于长安音。

罗常培著《唐五代西北方音》书影
高田教授从音韵学的声母、韵母和声调3个方面对汉藏对音材料进行分析。关于声母的问题,他首先介绍了切韵和唐代的声母系列,然后从无声无气音、无声出气音和有声音3个系列进行解说,详细列举了喉音、齿音、鼻音、轻唇音等,并归纳了河西方言的声母体系,认为其声母共5组26个。但是,高田教授认为,由于方言存在地区性差异,所以要完全复原单一的声母体系是非常困难的,汉藏对音资料只能反映出以K和0为代表的保守体系,以及不同时期的资料之间的差异。他发现,舌上音和正齿音的合并、摩擦音清浊的合并,以及齿头音和牙音的口盖音化不仅存在于现代西北方言,在整个北方语中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征。而对于全浊声母是否送气的问题,高田教授认为注音材料《开蒙要训》中浊音字有时用清音字来注音,但通常都是不送气音,并指出《大乘中宗见解》里的全浊声母不分平仄,全部用送气音来转写只是特例。关于韵母的问题,高田教授首先介绍了切韵及慧琳音义的韵母体系,然后从韵摄入手,分析了遇摄、蟹摄、止摄、效摄、流摄、咸摄、深摄、山摄等15项,最后对河西方言的韵母体系进行了归纳,认为其韵母共15摄79韵。他提出汉藏对音资料大多属于9、10世纪时期,而陆法言的《切韵》和慧琳音义皆早于这个时期,所以它们的韵母体系是无法完全正确解释这些对音资料的,必须结合语言变化的历史背景。
史文琴指出,高田教授对于模韵做了进一步的细分,而且还将鱼韵和虞韵清楚地区分开来。高田教授提出,《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道安法师念佛讚》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对音资料中的唇音字全部用-u来写,其余的对音资料则用-o来写的。还认为,鱼韵使用的是-i(-yi)、-u(-yu)两种标记法,而虞韵大多用的是-u的标记法。并在《寒食诗》对音资料中将鱼韵和虞韵分别假定为[y] [?]和[iu]和[?u]。关于声调的问题,高田教授认为应从调类和调值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但是在汉藏对音资料中可作为分析声调的材料甚少,研究有一定困难。
他认同邵荣芬提到的对音资料中存在全浊上声变去声的现象,但同时他认为这种现象是汉语史上公认的事实,在唐代就已证明了。但对于次浊上声变去声,他认为在现在的北方方言中,次浊上声应归属于清上声,而不是全浊去声。
高田教授还从人称代词、疑问词、结尾词、句末助词和疑问句等语法方面分析了汉藏对音资料,并在附录中转写了全部汉藏对音资料,添加了《开蒙要训》注音通用表、资料对音标和资料的图片。可以说,高田教授通过精准的资料分析,完成了现存大部分汉藏对音资料文本还原,研究方法新颖,结论具有说服力,不仅对汉语史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敦煌学及中亚语言史研究也影响颇深。
二、河西方言的语言史研究
高田教授的第二大研究领域是关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各民族语言,阐明中亚语言交流的实态。他认为,敦煌拥有汉代以来的悠久历史,多少代人一直努力经营该地区的居民,培养了其独特的文化与语言。这就必然形成了广义上的河西语言圈的一部分。在唐代以及吐鲁番统治时期,使用长安音仍是通例。但后来的归义军时期,寺院里的诵读佛经也开始使用河西音。而且,敦煌居民写下的归义军时期的语言材料极多,仅从汉字书写的表面来看是难以把握其实际情况的。尤其是文言的因素增加了,河西的特征就不能不变得更加微弱。然而理解了经过复原的河西音的背后,对各种写本的看法自然会完全改变,所以有必要从河西语言史的角度对敦煌文献整体试作重新研究。
1985年和1990年,高田教授陆续发表了《回鹘字音考》(「ウイグル字音考」)和《回鹘字音史概述》(「ウイグル字音史大概」)两篇论文,阐明回鹘字音的特点在于,虽是以中国西北部的河西方言发音为基础,但其使用回鹘语的音韵系统,没有声调的区别,声母和韵母页大大简化。这项研究成果开拓了理解西域历史和语言文化的新天地,给相关领域的古代突厥语、阿尔泰语及日本语言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启发,因此荣获了昭和六十一年(1986)度第五届东方学会奖。
高田教授在《回鹘字音考》中使用了两种佛书音注的小断片作为研究材料,一个是原东德柏林科学院所藏的《慈悲懺音字》,另一个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现藏的《法华经音》。
他首先从声调进行考证,发现两种资料中一半以上的字都是用其他两种声调的文字来注音的,几乎无视了平上去三声之间的区别,而且这些注音声调的归属与切韵系韵书是完全不同的。《慈悲懺音字》中牵(平)、遣(上)二字都用坚(平)来注音,排(平)、背(去)、败(去)三字都用贝(去)来注音,《法华经音》中私(平)、訾(上)、肆(去)三字都是用四(去)来注音,可以认为是完全忽略了声调的存在。由此,高田教授断定,这种忽略声调存在的现象,证实上述资料能够被用来证明吐鲁番曾经存在回鹘化字音的最大理由。接着,高田教授对两种资料文字的声母进行了考证,发现其出现的声母合并现象与汉藏对音资料的声母合并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他认为回鹘人应该是用音读的方法来诵读汉文佛典的,所以这种注音在形态上很明显是回鹘文。由此,高田教授得出的结论是,回鹘字音应该是以9世纪吐鲁番的汉语语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之后,这种字音出现回鹘化,并进入到回鹘字音的时代。《慈悲懺音字》和《法华经音》在吐鲁番的流行以及它的注音书的作成,应该是11世纪后半叶之后,而且很明显都是出自回鹘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古代回鹘民族应该有一种被引入到回鹘语中、被其音韵体系所吸收的,并且只存在于回鹘字音中的语音,高田教授在论文《回鹘字音史概述》中继续对《慈悲懺音字》和《法华经音》两种文字材料的韵母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两种注音资料在韵母的通用上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没有一、二等间的元音的区别,二是合口u介音常常被简化,三是i介音有时也被忽略,并且汉语本来应有的区别淡化了,同时在字音上表现出了回鹘语的一些特征。在这个基础上,高田教授推测,唐代时期的敦煌使用的是长安方言,但自786、787年开始,经历了前后70年的吐鲁番统治期,进而又在归义军政权下,这时期的长安方言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土著方言占据强势。而在9世纪中叶,回鹘被驱逐出他们的故地蒙古高原,迁居东部天山的南北两麓,在那里从前的长安方言仍然会以读书音的形式流传下来,同时也存在着用于口语的土著方言。
1993年,高田教授又撰写了《回鹘字注音的吐鲁番汉文写本残片》一文,以在柏林所藏的吐鲁番收集品中的一件在汉文各行间加上回鹘文字注音的汉文写本残片为研究材料。
经其考证,这个残片是一件利用某种佛典的背面书写的写本,使用的是草书体的回鹘文字和用木笔书写的汉字字体,应为元朝时期的遗存。经过对残片的复原和音韵特征的考究,高田教授认为,该残片的注音中所用到的回鹘字对音,应该是以河西型方言为基础的,自10世纪末逐渐形成的字音。
高田教授也对于阗语以及河西语言圈的其他多种语言进行了诸多论考,发表了《于阗文书中的汉语词汇》(「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1988)和《敦煌发现的多种语言文献》(Multilinguialism in Tun-Huang,2000)两篇力作,不仅对于阗文书中的汉语词条的音韵进行了仔细分析,还阐明了和河西方言渗透有关的语言交流和多语言生活的本质。
1988年,高田教授撰写了《于阗文书中的汉语词汇》一文,对散见于敦煌出土的于阗文书中的汉语词汇进行音韵学的分析。他发现,这类文书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汉语词汇,多为地名、官职名、人名等固有名词。然后,他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书中的汉语词汇进行了考证,推定出共计89条汉语词汇,对于其中的“六种”“政南”“新城”等词汇的推定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书中的于阗语通行于10世纪左右,应称之为新于阗语,因为在音韵组织上与保留较古形式的古于阗语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更好地考证中古音的声母、韵母是如何用于标记于阗文字,高田教授将(于阗)婆罗谜文字撰写的《金刚经》与于阗文书中使用的撰写法进行了考察和比较。
他发现从汉语音韵史的立场出发,大部分敦煌出土的于阗文书基本上都是以一种与《金刚经》相同的汉语方言为基础作成的,只不过文书是由多人执笔写成,是按日常使用词汇的音形所做的注音。它更倾向于语音,特别是通摄鼻音尾脱落的趋势在文书中比较明显,这在汉藏对音资料和其他河西方言资料中不多见,由此亦可见这类于阗文书之贵重,在河西方言发展进程的考察上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敦煌发现的多种语言文献》一文的主旨就是要把敦煌写本中关于敦煌地区流行的语言状况做一总结。基于这个出发点,高田教授逐项列举了粟特语、于阗语、梵语、回鹘文四种敦煌写本所见语言。之后,对于敦煌地区出现的藏语和汉语共存现象进行了详细解说。他指出,因为吐蕃在786—848年间对敦煌实行军事统治,既然统治者使用藏语,不难想象各级政府机构也在使用藏语,敦煌百姓也不可避免会接触到藏语,而且从敦煌文献中也发现,吐蕃时期的杂写经常与官方行政文书的开头一致,有的契约文书是汉人书写的,使用的却是藏文。9—10世纪河西、中亚地区摆脱吐蕃统治以后,藏文仍然占有很高地位,并常作为外交语言。敦煌出土的佛经抄本、汉藏双语文献,以及寺院和汉藏双语群体社区的存在都反映出敦煌地区出现过汉藏文共存时期。但是,高田教授认为,从汉代起敦煌就属于讲汉语的中原汉政权,虽然吐蕃统治时期对汉语的使用有一定冲击,但在归义军统治时期,汉语中的河西方言成为敦煌的主要语言。
三、敦煌音韵史料的研究
在音韵史方面,高田教授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敦煌本〈玉篇〉》(「玉篇の敦煌本」,1987)、《敦煌本〈玉篇〉·补遗》(「玉篇の敦煌本·補遺」,1989)、《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语言和敦煌写本的性格》(1992)和《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排字韵〉札记》(2004)等。
《敦煌本〈玉篇〉》主要是以英国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收藏品中的敦煌本《玉篇》残片为考察对象的。这部残片贴在S.6311《佛说善恶因果经》纸背,写在高27厘米的黄纸上。高田教授首先对敦煌出土的写本是否为《玉篇》进行了考证。他从部首和内部排序排除了写本是汉代许慎的《说文》和晋代吕忱的《字林》。但是发现,这个敦煌写本所引的书是《礼记》《尚书》,与顾野王的原本《玉篇》大量引自经书是一致的,而且这个写本在引用《内则》的经文之外又引了郑注,更加符合原本《玉篇》的体例。
高田教授认为,这个敦煌本《玉篇》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直音的注音方式,这点与原本《玉篇》有所不同。原本《玉篇》虽然也有直音的方式,但是还是主要以反切为原则的,然而这个敦煌本的注音全部使用了直音的方式。因为反切注音法的使用对于作者和读者的要求较高,而直音方式更容易为民间所接受,所以高田教授进一步推测,这个敦煌本应是为提供民间使用而经过改编的《玉篇》的众多版本之一,即为顾野王原本《玉篇》的大众化改编本。后世的《玉篇直音》《春秋直音》和《九经直音》等书的存在,也为使用直音注音法的字书经常为民间所需要提供佐证。高田教授在发现敦煌本《玉篇》的面貌与顾野王的富有学问气息的原本已有相当的差异后,对这个敦煌写本的年代进行了推测,认为其大概是唐末五代的9或10世纪前后的写本。但是,后来高田教授获知这个写本是8世纪之物,马上对之前的推测进行了修正,认为有必要稍微上溯《玉篇》的改编及其大众化的势头出现的时代。
《敦煌本〈玉篇〉·补遗》是对《敦煌本〈玉篇〉》的补充。敦煌本《玉篇》的残片共有两个,一个藏于英国伦敦,高田教授于1980年访问大英图书馆时亲手考察过这个残片。另一个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奥登堡,高田教授称无法看到其实际面貌,只能通过孟列夫等编的目录揣测其大略情形。但是不久,高田教授发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奥登堡收集的敦煌本《玉篇》残片的照片,实际上已经刊载于陈祚龙的《敦煌古抄文献会最》(1982)。因此,高田教授依据这幅照片对前文《敦煌本〈玉篇〉》进行了补遗。
在文中,高田教授就对英俄的两个残片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它们使用的纸张的尺寸和颜色均相同,而且注音都使用的是直音法,标记为红色,所以他推断,这两个残片属于同一写本。在获取俄藏残片的照片后,高田教授逐行对该残片的注文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他考证,该残片内容共11行,不是孟列夫所编《目录》记载的6行,而且《目录》最初记录的写成红字的直音注音字“莫”,实际上应该读作“英”,是对“影”字的注音。高田教授还指出,俄藏残片中大量援引古书尤其是经书的经文与注这点,与公认的原本《玉篇》体例是相符合的,特别是它的部首的排列方式,更能表明《玉篇》民间流传本的多样性。
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记录了他经由南海进入印度,归途中路经西域的所见所闻,被视为玄奘《大唐西域记》之补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敦煌出土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写本为该书目前仅存之本,且被学界认为是慧琳《一切经音义》中所载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一书的节略本。针对这个论断,高田教授撰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语言和敦煌写本的性格》一文,从汉语史的角度出发,探讨写本使用词汇的若干语言特征,同时立足于其他旁证资料,提出了敦煌出土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写本为《慧琳音义》所据之定本的草稿本的假设,并加以证明。
高田教授发现,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虽然以书面语为基调,但其中混杂口语的成分,如“共”“向”“個”“裹”等常用于口语的词均在写本中出现,特别是在诗歌中经常使用的“足”字出现频率最高,达到了27例。在考察口语成分的同时,高田教授还发现,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存在很多不正规语法的例子,行文颇为粗杂,但是与《慧琳音义》所据之定本的相似度很高,两者之间出现了很多字句异同现象,如敦煌本中“胡蜜”“播蜜”两处,在慧琳所据本中分别作“胡蔑”“播蔑”。由此,高田教授再结合学界将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认定为8世纪之物,以及慧超撰写此书时年纪尚轻等已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推论——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非慧琳所依据的三卷之定稿本,而可看作是一种属于草稿本系统的写本。
2001年,高田教授在台湾举办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了解到莫高窟北区石窟新发现的《排字韵》残片一事。当时,敦煌研究院的彭金章教授介绍了文献《排字韵》的残片及其价值,并认为该残片是《广韵》以后的一部重要的而已失传的韵书,对此,高田教授在会上也提出了该残片大概是《礼部韵略》的一种之意见。其后,他对此韵书残片展开了进一步研究,注意到该残片的内容其实与有名的王文郁的《新刊韵略》完全一致,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排字韵〉札记》一文,意在指出敦煌文献《排字韵》残片与王文郁的《新刊韵略》的一致性的同时,提出关于发现该残片的意义的若干要点。
高田教授认为,北区石窟发现的《排字韵》是刻本的两页残片,每半页有13行,《新刊韵略》也是每半页13行,而且正文的内容完全相同,包括注释、反切、又音、重添字在内,文字全部一致,除了是否排字的重大差异,形式上也有许多相同之处。特别是韵部之间用鱼尾形的记号加以区分这点,非常明显地反映了《新刊韵略》与《排字韵》的继承关系。并且,是否排字完全是出于民间出版商的创意,是为使用者的便利而考虑的版面设计,可以说是《排字韵》作为《新刊韵略》的一个坊刻本的富有特色的形式。在此考究的基础上,高田教授进一步提出,作为未经增字版本的《排字韵》应更名为《排字新刊韵略》或《排字新刊礼部韵略》较为合适。
高田教授的这些论文加上前述的回鹘语、于阗语等河西语言的研究成果,译为中文后均收录于《敦煌·民族·语言》。这本书囊括高田先生卓越的研究成就,在语言史和中亚史等相关领域广泛流传,得到了中外研究者的高度赞誉。
四、致力于中日和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
高田时雄教授以主攻的语言史研究为中心,涉足诸多学问领域,统合各个领域知识,高识远见,不但继承了已臻细腻的传统中国音韵学,而且在日本的东方史研究传统基础上,将欧洲文献学、东方学的研究视角融合在一起,对于敦煌写本及敦煌社会复杂的语言状况提出了新的见解和新的框架,构建了古汉语研究的大方向。1983年4月,高田时雄协同森安孝夫、熊本裕、武内绍人、吉田丰四位在日本关西地区(京都、大阪)从事西域语言和历史研究的学者组成了“青年敦煌者协会”。他们利用敦煌文献分别在回鹘、于阗、汉、藏和粟特文领域确立自己的地位,同时准备合作研究《善恶因果经》等文献,使敦煌学京都学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专一性和综合化研究的新特征。
随着敦煌文献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公开,各国敦煌学者加强了在各个研究领域的联系。高田教授积极致力于国际,特别是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不仅在日本国内是东方学会、日本中国学会、日法东方学会等的会员,在国际上还担任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干事长。同时,他还兼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发行的杂志《东方文献遗产》的海外编辑员,以及《中国语言学集刊》的编辑顾问等职务。
从1990年起,高田教授联络日本和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开设了“中国语史的资料和方法”(1990年4月—1993年3月)、“中国音韵史研究”(1993年4月—1998年3月)、“十六、十七世纪亚洲语言接触”(1998年4月—2002年3月)、“王玄策研究班”(2002年4月—2006年3月)、“西陲发现中国中世写本研究班”(2006年4月—2011年3月)、“中国中世写本研究班”(2011年4月—2014年3月)等一系列专题研究班。
系列专题研究班从2007年开始至2019年出版13期的《敦煌写本研究年报》,刊登了中日两国以及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这项活动不仅促进了中日敦煌学研究者之间在汉语史等领域的成果交流,进而有助于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此外,他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参加俄藏敦煌文献轮读会,积极与中国大陆的张广达教授、荣新江教授和郑炳林教授等,以及中国台湾敦煌学者郑阿财教授、朱凤玉教授等,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并经常赴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举办学术讲座。2012年12月6日,高田先生应中国敦煌研究院邀请,做了题为《日本敦煌学的历史和特点》的学术讲座,详细介绍了日本敦煌学的特点和历史发展阶段。
高田教授一直把自己作为敦煌文化的传承者与研究者,秉承敦煌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正视敦煌及敦煌学的历史和现实,积极推进敦煌学各个领域的发展。2014年,为了纪念高田教授退休,京都大学东方学研究论集刊行会编的《东方学研究论集》刊登了一文《高田时雄教授之学问》,逐项列举了高田教授运用语言学和文献学在分析和研究敦煌写本中取得的成果,高度赞誉“其学问之深湛、贡献之卓著,在日本国内外有口皆碑”。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新浪微博




